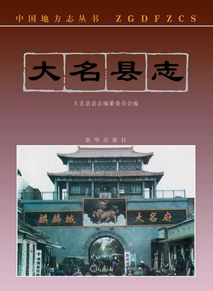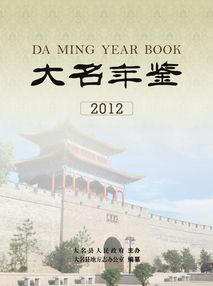我一九〇六年生于井店,原名平俊义,字杰三。家庭比较贫困,父亲经商,后来还算过得不错,七岁上小学,后到濮阳城里上高小,一九二三年暑假考入大名七师。小学时,课堂上讲国民小学课本,堂下读私塾。我对老书不感兴趣,对新课本容易接受。濮阳全县会考时,一千多名学生,我考第二名。上高小三年,不论月考、期考,都是第一名。当时,我开始接受了新思想,读过《新青年》杂志。大名七师的校长、教师部比较进步;一些有影响的进步报刊邯能看到,印象比较深的有《独秀文存》、《胡适文存》、《吴虞文录》、《语丝》、《小说月报》等等,涉猎面很广,什么东西都看,也没有什么选择。主要是接受爱国主义思想,反帝反封,痛恨当时社会的腐败,要迫求一个新的中国。
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运动波及到大名,教育界成立“五卅”运动后援会。我也参加了这一活动,受到了不少的教育。北伐战争开始,自己很受鼓舞,觉着中国有了希望。一九二六年昏假,我和李素若、王正回到濮阳,发展国民党,迎接北伐军。淤闲籍的七师同学和大名十一中的同学在濮阳城里开了个会,加入国民党,并提出组织农民迎接北伐军的口号;还发了三本书:卜卡图的《通俗资本论》、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和《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从此就算参加了革命。接着,我就回到了家乡组织国民党区分部,发展了一批党员,如陈幼武、常秋圃、张春阳、喻屏等。
一九二七年冬,赵纪彬、李大山、刘大风等共产党员在井店高小活动。在这个时候,除了陈幼武、常秋圃没转入共产党以外,我和其他同志都转入了共产党。这一段活动很有成绩,比前一段组织农民、迎接北伐的活动有声色,因为农民不管你北伐不北伐,他们没有兴趣,说也听不懂。我们加入共产党后就读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彭湃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和恽代英主办的《中国青年》杂志。这时候,也知道结合农民切身利益开展工作。
井店、千口、化村三个党支部同时建立。并店的工作开展得比较快,主要原因是这里的阶级矛盾比较突出,掌握实权的土豪劣绅王礼、陈清池派捐加税,名目繁多。郭连元包揽各种税收,又随意加码,这样,不仅广大农民受害,连中小地主、商人都不满意,受到很大痛苦。所以,农民协会、商民协会就很快地组织起来了,形成了一个反捐税、反压迫的统一战线。
一九二七年底和一九二八年初,由农民协会、商民协会发起,同当权的王礼、陈清池开展算账斗争。当时,替他们管账的郭振三是我们的党员,公布了他们制造的假账,激起了群众的义愤。一个会议推倒了王礼、陈池清,选举我和陈修士(比较开明的绅士)为正副市长。这个斗争声势很大,规模也很大,但是搞起来怎么办了方向不明确。我就去千口找赵纪彬,李大山请示办法,我要求四乡支持,争取合法化。我们商量后,我就去濮阳县政府备案。这时,城里的实权掌握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八集团军刘振华部队手里。他们还有革命气息,没有反共气味,我先找到李素若,通过他又找到县长李鸿钧,谈了我们建立井店市的情况,第三天就发给了我两张委任状。同时,刘振华政治部有个共产党员,他给我和李素若谈,你们要抓紧建立县党部,你们要不建,地方绅士搞起来对你们不利(这时,濮阳县的大绅士郭方堂、桑建之等都被抓了起来)。我们俩都同意他的意见,随时搞起了县党部筹备处,我任筹备处主任。在县里活动了十来天,又回到千口,向赵纪彬、李大山作了回报、当我回到井店时,因为王礼、陈清池的势力很大,表面上他们虽已不当权,实际上还掌握实权,趁我不在家,他们又把民团拉了过去。新当选的副市长陈修士一看这个形势,他也不敢接受委任状了。当时,我舅父对我也有压力,因为他是陈清池的朋友。这种情况使我骑彪难下,我又去千口找县委请示办法,要求四乡支持。赵纪彬、李大山表示不好办。我就提出到县里搞县党部,他们同意了我的意见,我到了县城,很快建立了县党部,李素若的书记长(共产党员),其它有李步庭、张之平、张才三、王亦华,这些都是共产党员,我分工是监察委员兼管武装(民团、公安局的政治部主任),还兼任党攻洲练班的教育长。这时,中共地下县委赵纪彬派蔡兆林到这个党政训练班任干事,做地下党的工作。他任支部书记,发展了一些党员,秦廷瑞、穆俊敏都是在这里入党的。
温邢固算账斗争中,我和蔡兆林带着民团武装,把他父亲蔡鸿宾扣押到县党部查对账目。不久,蔡兆林叛变,造成温邢固事件,刘汉生、王卓如、李大山、赵纪彬被捕。他们在县里拘留期间,我和李素若等同志作了许多掩护和排解工作,遭到了反动势力的非难和控告。从此,我们这一届县党部被查封,李素若、张之平被通缉,我也离开了濮阳。县党部改组,右派势力掌权。
蔡兆林叛变后还咬了我一口,我在大名过了一堂,他说我是共产党,我税他是共产党,他拿出党政训练班的同学录作证据,我说这是他一手填写的,我根本不知道。就过了一堂,法庭拿不出真牛实据,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温邢固事件后,我又回到大名七师上学,一九三O年毕业后,返回濮阳高小任致;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组织读书会、抗日大同盟,发展党团组织,不久,受到邀缉,离开濮阳。
一九三〇年冬到了北平,先在南郊、在长辛店,后又到唐山,都是搞党组织的恢复工作,也都是刚一作出点成绩,就遭到了敌人讨破坏,如在南郊,在名义上我是黄村民众教育馆馆员,实是做地下党的工作,馆长还算不错,他知道我是干什么的,还给我汀招呼,叫我注意,不要叫他为难。经过半年的工作,才到搞出点成绩,一个飞行集会作演讲,斗争了对方,暴露了自己,被馆长“礼送”出来,我离开三天,也下党组织搞了—次暴动,也失败了。我叉到长辛店,作恢复党组织工作,才到有点起色,因写给省委的报告被转送到共产国际东方职工部,在—个什么通讯上刊登出来:这个负责办通汛的人叫牛兰被捕了,国民党政府抄走了这个报告,长辛店的工作又受到破坏。我又到唐山作恢复工作。一九三一年底回到北平,我和河北省委的马惠之、王德等四个同志在一起开会。这时,中央已决定调我到陕北,因为出了叛徒,就在这个交接会议上被捕了。这一次,是北平市和河北省党组织的一次大破坏。一九三三年底出狱后,告假回家养病。一九三四年秋天,到清丰师范任教育长。我这个人在冀南也不好潜入地下,因为准部知道我是共产党,在北平坐过监狱,这时,我就总结经验教训,总觉着这几年的搞法不行。究竟怎么办?以后搞整风,才知道执行了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都是“左”的。当时我也被认为是右倾,不敢于。通过整风学习,心里才明白。
回想起来,在清丰这一段我的方法是对的,也觉着踏踏实实做了一些工作,为革命积蓄了一些力量,培养了人才。如几个县委书记陈尔东、姚伟杰、谷丙方、付学阶等都是这个时候培养出来的。这时,清丰三个学校:一个女高,一个男高、一个师范。我虽在师范,其它两个学校的进步学生也知道我,我只做一些启蒙教育工作,上海的进步刊物都寄给了我,学生传着看。我还有个有利条件,就是什么课都能上,除了物理化学以外,美术也能上。哪个老师有事,我就代替;所以,我在学生中接触面很广,我这样做,也埂于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对有入党要求的人,我不直接介绍,只作间接介绍。因为我的组织关系还在北平,在这里只和直南特委的主要负责人发生关系。先是和王从吾同志接触,从吾被捕后,又和张增敬接触,增敬被捕了,他又把我介绍给张玺。
抗战一开始,清丰之所以能够很快地轰轰烈烈搞起来,和这三。四年的工作基础是有关系的。
一九三七年底,刘大风同志以特委代表的身份到清丰找我,讨论如何贯彻实施党中央的抗日十大纲领,研究恢复沙区党组织和建立抗日救国十人团的事情。先在清丰搞了一段,我担任十人团的大队长,晁哲甫、安法乾负责恢复清丰一带党的组织。时间不长,十人团一部分编入了四支队,一部分变成了抗日救国会。我又被派回井店,先找到刘玉峰、张怀三,建立抗日救国十人团,恢复党的组织。后又同丁树本达成协议,我拿着老丁的信和特委的信,在井店组建濮阳专区抗日八大队,我任大队长,张复武任大队副,杨法秋为董事。在杨法秋民团武装基础上,先在井店搞起了一个中队,王从吾、刘汉生等同志也分别在化付、千口一带村庄组违了两个中队。这两个中队的枪支是从地主家里和旧民田的手卫动员出来的。这三个中队名艾上是一个整体,实际上没有在一起集合过,是各搞各的。表面上是丁树本命名为濮阳专区第八大队,实际上是濮内滑中心县委领导下的抗日武装。这时,我是中心县委书记。不久,化村、千口两个中队的百十人、枪被编入特委领导的91支队第一中队,井店这个中队因为张春阳怕被改编,怕被吃掉他的武埃:以强凋保家为名,指示他的侄子张复武把人、枪拉了出去,我去找他,他不跟我见面。后由六八八团抓住了张春阳,把枪追回,罚款两千元。又把张春阳处决了。当时也觉察列对这件事的处理有些过头,张春阳不应杀掉。这时河西的土匪势力很大,过河抢劫,屠杀小槐林+四支队又奉命调走,群众对我有些埋怨,现在回想起来,四支队如果不凋走,对发展抗日根据地和保卫家乡更有利。为了保卫地方、抗御土匪,我们灭利用杨法秋的武装和八大队井店中队的一部分武装,联合组成了四县联防(濮、滑、内、汤)地方武装,各县都有人参加,并推举杨法秋为总团长,还出了联合抗日的布告。为什么要利用杨法秋?因为他和河西的土匪有拉拢,在他们眼里也有威望,当然他对我们也是利用,不是依靠。但是,时间不久,我离开了这里。后来,这个四县联防也变坏了。
一九三八年三月,直南特委根据同共合作的需要,派我带三十支人枪到丁树本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担任政治部民运部长,罗士高同志为政治部主任,濮内滑中心县委书记换成王玉振同志。
一九三八年九、十月间,我又从丁部调到冀南行政区参议会,搞群众团体工作。一九四一年五月调太行搞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作筹备工作,选举产生了边区政府,我任副秘书长。一九四五年冬,又凋晋翼鲁豫中央局任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副秘书长、秘书长兼统战部长。后来,晋冀鲁豫中央局又变成中共中央华北局,我仍兼统战部长,华北局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一九五四年华北局结束,我就詖调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在此期间,还被选为一届人大代表,全国政协三届常委、四届秘书长、五届常委,党的“八大”代表。
常务副部长的工作是很忙的,机关党的工作,内务工作,主持部务办公会议,协调各局、室的工作。我这个人没有重大建树,只是长期的机关工作养成了一种勤勤恳恳、严肃负责的工作习惯。
统一战线工作是我们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在战争年代是如何团结更多的人跟我们一道打败敌人,分化敌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就是如何团结更多的人跟我们一道搞社会主义。这里政策性很强,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时,有的因政策界限不清,错划了一些小资本家、小业主,通过调查研究,我们提出了区别“三小'的建议,使全国近五十万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恢复为劳动者;在划右派问题上有严重的扩大化,后来毛主席提出来要逐步摘掉百分之七十的帽子,每年摘一批。一九六二年春末,我主持召开全国“改右”工作会议,事前部务会议研究如何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提出摘帽从宽、生活上照顾、错划平反的正确意见。在“改右”工作会议上我也是这样讲的。但当时中央正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后来变成了八届十中全会,确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我们为右派说话。有些同志说,我们都是“瓜、菜、代”,如何照顾右派生活了我们的干部下放,怎么能把右派调回机关?李维汉同志给我打电话通气。这次“改右”会议没有实现我们的建议,会后不久,就批了李维汉,我也受到了批判。直到“文革”后,我和李维汉都恢复了工作,才在党中央支持下,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右派得到了改正,为四化调动了积极性。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一九六七年元月,中央统战部就被夺了权,统战部就站不起来了,我是一九六六年九月就不上天安门了,有通知我也不好意思去了,接着就是挨批斗,七年被监护,三年被流放(焦作),一九七七年底回到北京,一九七八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就是先做点工作,一九七九年元月恢复副部长工作。几十年来,日过头看,李维汉主持统战部的工作是对的,他是我们党的老资格的领导人,早年左右倾错误都犯过,后来他从实践中认识了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路线,所以建国以后他一直是对的,后来毛主席的指导思想错了,他就成了“三反”分子。这在我那篇文章(指一九八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四版,纪念李维汉九十诞辰)中已经说清楚了。
统战部的外事活动主要是兄弟党来交流统战工作经验,我除了参与这项工作外,一九五三年第三次赴朝慰问团我参加了,贺龙的团长,我是副团长,是华北分团长,一九五九年参加过党政干部休假酗,到苏联去过一次,那时中苏关系已处于紧张阶段,我们去了只讲友好,不讲政治;一九八一年我参加了全国政协访美代表团,我是副团长;一九八五年政协组织的港澳访问团,我也去了,主要是交识新朋友。
我这一生,几乎是做了一辈子统战工作,有成绩,也有错误,有经验,也有教训,整过人,也被人整过。我经历了七次大的政治运动,五次是我领导,如“三查三整”“三反五反”、肃反审千、反右派斗争是我领导的,因为我受过批判,领导运动也是右的,但尽管右,也犯有扩大化的错误。不管怎么样,我对党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现在,我年事已高,责任都卸了,只有一个顾问委员会委员,但还是照常上班,并不感到轻松。
(史其显、温民法、刘静轩根据谈话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1986年1月4日、6月20日于北京)
——政协内黄县委员会内黄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史志资料选编 第2辑 内黄县古今人物选.,1986年09月第1版.